论傅天虹的诗
——一种自传式读法
张立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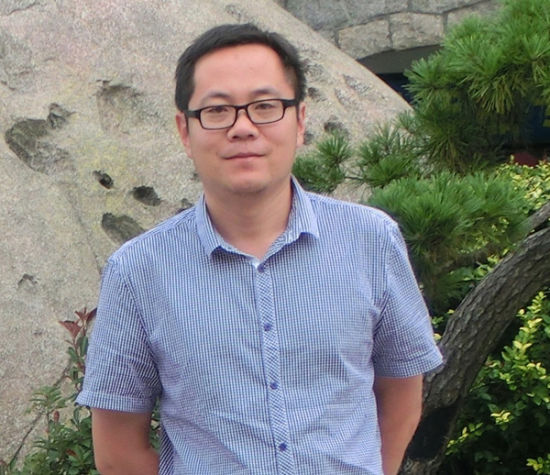
关于傅天虹的诗可作为他自传的观点,数年前就已有一些研究者指出。而诗坛元老屠岸先生更是在为傅天虹新诗选集所做的序言中强调:“傅天虹写诗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他的全部诗作如果按编年方式排列起来,就是一部自传。说是自传,并不降低它的文学品味。或者说,是一部诗的自传。何以这样说?因为天虹全部诗作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真。真实的经历,真实的际遇,真实的思索,真实的情感,真实的遐思,真实的梦想……”尽管,我们无法将傅天虹的诗完全作为诗的自传或曰自传的诗,但自传意识显然是傅天虹诗歌最为突出的方面;自传意识取决于写作的历史和写作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言说傅天虹的诗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自传式的写作需要相应的解读方式,这一点,一旦与傅天虹具体的写作结合起来,便不难发现:它理当成为研究其诗歌的重要课题!
一、始于童年的出发点
作为童年记忆的追溯,傅天虹通过诗真实记录了自己儿时的经历。在《童年》《摇篮曲》《小雏鸟》《我不是一个乖孩子》等作品中,傅天虹以儿童特有的思维、语言方式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体验。“我最初的世界/是外婆唇边的摇篮曲”(《摇篮曲》)单纯、透明,不加修饰,可视为“诗之自传”的起点。但是外婆于耳边吟唱摇篮曲而非母亲,又使傅天虹的诗笼罩着淡淡感伤的色调。像那只在“树下扑腾”、“没长全翅膀/抖动得多么可怜”的小雏鸟,像《朦胧的眼睛》记录自己成长的历程和不幸的遭遇。傅天虹的“童年叙事”既有其真实的生命体验,又有十分明显的心灵创伤痕迹。傅天虹1947年生于南京,自幼没有见过父亲,后又失去母亲的呵护。他在外婆的抚养下长大,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他跟从外婆姓杨,后到处流浪,过早体味到人间冷暖。这种不幸的童年经历,使其在真实叙述时难免带有一种痛感,也难免将真实的体验融入诗中。《我不是一个乖孩子》《朦胧的眼睛》都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写下了自己的遭遇,令人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受到灵魂的触动。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健全的童年、过早接触社会,也使傅天虹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很早就形成了介入生活的行为方式以及观察、理解世界的角度,直至实现其自我形象的确立。通过阅读这些诗篇,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敏感、真诚而又坚强的傅天虹。在《我不是一个乖孩子》中,诗人多次重复“莫责怪我/我确实不是乖孩子/但是/我会写诗”,表明儿时漂泊无依的傅天虹很早就迷上文学、爱上诗歌,而诗歌也确实是其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张着一双“朦胧的眼睛”,他不仅书写了想象中的母亲,而且也写下自己的孤独、无助,找到了倾吐心曲、缓释焦虑的途径,他最初的思与诗就这样抵达了一个契合点。
经历特定年代的“自传”注定充满生命感并以此见证了历史的复杂与曲折。傅天虹曾在《邻居》中写过三天没有进过一点粮食的“黑七类”的孩子;在《尽管》中写过“黑七类”的沉重铁牌,“落叶般的唾弃埋没我青春的光彩”,“尽管歧视和偏见把我逼上悬崖/潮水般地凌辱激起我无限的悲哀”;又在《春天里》写下“冰冷的脸”、“冰冷的关系”、“冰冷的街市”、“冰冷的土地”,直到最后写出“春天/生活在冬季”的体验。但作为一种个体的回声,傅天虹又以此写出了一个不屈的、在逆风中成长的“心灵史”——
大雾湮没了山路
心不迷途,仍能采到远方的花束
朔风吹黄了苗圃
心不僵冷,仍能萌发不屈的新绿
埋葬地层不忘春天的呼唤
蒸为水气不忘养育的河谷
冻成冰棱不忘精纯的操守
山崩地裂不忘石质的坚固 ——《心迹》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傅天虹从未放弃对生命和理想的追求。他不屈服现实的压力,也从未过多抱怨生活的无情。在更多情况下,他是以坚守和抗争搏击逆境并越挫越勇,这样的表达方式使其诗歌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对应性结构”:尽管氛围与背景有些黯淡、苍白,但傅天虹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充沛的情感突破了诗歌中的环境障碍,他的诗歌自传也以此迈出了踏实的第一步。
二、源于土地的卑微意象
出于对自身境遇的认同,傅天虹早年的诗曾多次出现卑微、弱小的意象。比如,在《春天受到责难》《放开我》《青春》《野草》等作品中,傅天虹多次使用了“野草”、“小野花”等意象,并将其和第一人称“我”联系在一起。“我只是一棵草/一棵伤痕累累的小草”(《春天受到责难》);“我只是旷野里/一朵柔弱的小野花呀/春天开点淡淡的花/秋天结点碎碎的果/我写诗/有什么罪过?”(《放开我》)“野草”、“小野花”等意象的使用,使傅天虹的这一类诗可以被纳入到咏物诗的范畴,而“我”的介入和第一人称肯定性陈述又使之拥有自况与自喻的含义。意象之卑微、弱小折射出傅天虹对自己渺小的认同,而实际生活中诗人也确然谦和、友善;卑微、弱小的意象多植根于土地并常常直接于诗中呈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反映诗人的写作植根于生活、接地气,这一点又可以作为傅天虹早年生活经历的写照。
傅天虹的咏物诗是其诗之自传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步入青年、走上社会之新阶段的人生自况。通过自我书写,傅天虹展示了他性格、气质的另一面,此即为承认自己的卑微、弱小,但从不屈从于命运本身。“我没有悲伤/在角落顽强成长/从没有成为一朵花的梦想/我愿在草的世界/一辈子潜心吟唱”(《春天受到责难》);“我是野草,是大地无私地推举/我不怕风的侵袭/我纯真,渴望绿化荒野/渴望奉献,渴望给母亲披上一件翠衣”(《青春》);“受苦受难,它从不计较,/仍把活力输送到每片叶梢。/用芽,传播春天的讯息,/用实,迎接金秋的来到。”(《野草》)诗人借助“野草”等意象书写自己的人生,并随着时间的延展灌注于写作之中,其性格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历史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一种经验化,那么,在傅天虹的诗歌中,其自强、自立的品格是贯穿始终的。当然,随着阅历的增长,诗人在表达自身上述特征时也呈现出开放的状态。以《跪石羊》为例,诗人借助明孝陵旁跪卧的石羊,呼唤弱小者的崛起,“唱一支自己的歌”;以《酸果》为例,诗人通过成长史式的书写,写出“一枚酸果”,历经万难后终究结实的过程。这些相对于历史、现实、自我的书写,使傅天虹的“自传”具有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当然,最能体现傅天虹自喻的是有“虹”意象的诗——
——是一束长长的丝哟,
从我的心头抽出。 ——《虹》(1981)
一种七彩
凌空悬写的
一笔
是我小小的自尊 ——《自尊》
初晴
我便匆匆抹上
自己珍藏的
一道血色 ——《虹》(1988)
虹是悲哀的
由于某种风的缘故
它注定要
消逝在你的瞳孔 ——《雨后》
“虹”是雨后初晴的结果;“虹”绚丽多彩,但又很快消逝;“虹”来自于天上,和诗人同名。但傅天虹似乎更注意“虹”的生成:源自心头、珍藏的血色以及稍纵即逝,“虹”来自于诗人的心底,凝聚着诗人的自尊,为此他更加珍视“虹”的出现。与早年习惯使用的“野草”意象相比,“虹”的自喻是另一种生命状态。在我看来,它的出现与诗人心灵超越有关,在经历一次次风雨之后,傅天虹更加偏爱“虹”,即使它只是一个瞬间,但其隐含的盼望、斑斓的色彩以及释放重压的快慰却成为诗人一生难以忘怀的永恒。
三、两岸四地的人生游历
傅天虹于70年代末结束自己的流浪生涯,回到出生地南京,并由此开启他真正的诗歌之旅。南京时期傅天虹的有较为显著的青春时代特征。“祖国的远景浓缩在心里,/谁还吝惜这青春的血液!”(《致“答案”》)诗人有理想、有抱负,渴望追求生活的答案。经历多年的漂泊,终于回到故土、翻开新的人生篇章,年轻的傅天虹可谓既感慨万千又踌躇满志。对于正在经历的人生阶段,他说“我是野草,我是露珠,我是小溪/我是一串青春的音符呵/我纯真,我晶莹,我新鲜/风的翅翼驮着我交响的乐曲”(《青春》);对于现实与未来,他又大声疾呼:“祖国,请相信,/我会成荫!/青枝竞发的大地上,/会投下我的倩影!”(《萌》)与这些格调昂扬、积极向上的诗句相比,傅天虹献给青葱岁月和南京的歌显得沉静、舒缓。《根》《南京杂咏》等是诗人思考人生和历史所得。在这些作品中,傅天虹将自己的体悟和感受融入诗行,读者也以此看到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青年诗人。
按照朱寿桐的说法,“诗人天性,令傅天虹告别了前程似锦的大陆生活,他怀着突破两岸天堑,以诗会友促进诗艺交流的强烈愿望,於八十年代初涉足香港”。尽管在此之前,傅天虹的诗作已频繁发表于海外,但初入香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傅天虹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拼搏精神成就了他。正如他的《慈云山木屋歌》写有“小小的巢中”、“恬恬地飞出一群诗雀”。香港时期是傅天虹诗歌创作的飞跃期,同时也是其积极投身于诗歌社会活动的时期。有感于文化语境的差异,香港时期的傅天虹开始仔细打量这片“寄居地”,并逐渐融入其中。他的《香港组诗》《写于香港》《夜香港》《香江印象》《香港剪影》《香港风景线》《香港风情》等作品,多以现实的笔法、敏锐的眼光,写出一座现代大都市的繁华与冷漠、富庶与贫穷及人生百态,此时傅天虹的诗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哲理意识。
1991年迁居澳门之后,傅天虹的视域更加宽广。由于离港来澳本与他者的诬陷和诗人的毅然决然有关。是以,来到澳门的傅天虹更加珍视诗歌本身与诗歌交往、活动的纯粹性。此时的诗人经常往来于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之间,题材与眼界有了更大的拓展,诗艺上也有了更多的吸纳与自由。他的《武夷群峰》《观音堂三首》《澳门大三巴偶感》《澳门新口岸沉思》《重访秦淮河》《梦断西湖》等,多将自己的游历和诗情结合在一起,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既显示了诗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又显示了诗人寄情山水、感怀生命的写作状态。此时,傅天虹可作为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而经过多年的洗礼和锤炼,其诗歌本身也显得更为自然、圆熟。
傅天虹曾将自己所编的《傅天虹诗存》分为四辑,除第一辑“童年的我”之外,余下三辑即“金陵早春”、“港岛虹影”、“四地沉吟”恰为其两岸四地人生游历的生动记录,同时也可以作为其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贯穿这些阶段的重要线索是介入、迁徙与回复,它们与傅天虹的生活历程紧密相连,是其人生轨迹的外化与诗意书写,呈现了一代诗人傅天虹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见证了诗歌自传的丰富性与跌宕起伏。
四、“诗之自传”的艺术风格
傅天虹以诗为自己书写自传,这决定他的诗首先从内心深处流淌而出,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感和实录特点。从最初的漂泊到两岸四地的人生经历,傅天虹可谓一路走来、一路写来。“自传”的诗意追求使其诗总是将第一人称“我”作为抒情主人公,并由此实现诗中之“我”与现实之“我”的有机融合。即使那些没有使用“我”之人称的诗,傅天虹也常常不自觉地使用我之视角书写,只不过,此时的作品由于主语的省略更倾向于一种哲理的判断,并由此带上了自喻的风格、成为自己的写照——
仿佛山火并不可怕
一藤新花
坚持它的探求
在朽木上攀爬 ——《牵牛花》
经历了多年的书写,傅天虹早已熟悉如何将自己融入诗行之中,他的诗有丰富的情感,有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他是一位真正具有浪漫抒情气质的诗者,他的诗也因此和其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将傅天虹的诗从风格的角度予以划分的话,那么,在经历早年的自述和青春期诉说之后,傅天虹的诗越来越倾向于厚重的历史和自然风光。正如傅天虹的诗中,咏史、游历的诗篇占有相当的比重。傅天虹的“自传”倾向于稳定的价值判断、喜爱寄情于山水,这种符合浪漫诗人风格的书写,其实显示了傅天虹纯净、本真但又不失坚定的内心。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傅天虹是一位有理想、执着于追求梦想的诗人。“情绪不可按捺/青藤蓄积着/浓墨之势/走笔//相互扶持着/一对飞鸟/沿着蜿蜒的小道/走向天之尽头//山的剪影/是一幅不朽的画/获得了/落日的尊重”(《山巅》)。“相互扶持”让人想到了一种中年心态和相濡以沫,但从“不朽”、“尊重”等词语,我们可以读出诗人壮心不已的情怀。的确,从早年的坎坷经历,到青年的看尽人世沧桑,傅天虹体味到了生命的意义,但无论怎样,他都不甘心于平庸,他总是将自己的理想融入诗篇进而形成一种诗歌的风格化。他的诗在见证其生命史历程的同时,也见证了时代的变化,而其内容之丰富、跨度之长、生命力之旺盛,均使其堪称一部自传,而诗人本身也因此成为诗坛的常青树!
当然,如果从诗艺的角度上看,傅天虹的诗同样从不缺乏技艺。在《残雪》中,诗人曾有——
金鱼缸破裂於偶然
失去形状的水
流浪
成了唯一的语言
何时炊烟才能丰满
我期待一部诗丛
能用梦中纯白的和平鸽
设计封面
诗中的情境设置,让人看到一个在书写自己的过程中始终注意诗歌技法的诗人:他总是在诗中表达自己内心的律动,他如此理想化,以至于憧憬、积极向上是其永恒的主题。抒情主人公期待“一部诗丛”、“设计封面”,其强烈的主体性与题目“残雪”结合在一起,又会让人读到一个不屈的灵魂。
应当还有许多内容,当我们以“自传式”的读法,阅读傅天虹的诗。如果我们从爱情诗的角度进入傅天虹的世界,或许会获得另一道风景,只是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傅天虹是当代诗坛经历最为丰富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极具风格化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堪称一部人生自传,而其需要读解的内容还有许多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