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詩學——百年中西詩歌翻譯對漢語新詩的貢獻
海 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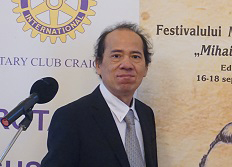
十年前,筆者選編《中西詩歌翻譯百年論集》(2007)秉承一大原則,即立足於詩人譯者的視角,注重詩論譯論構建及創作翻譯並舉,互為佐證。編選論集旨在梳理與總結中西詩歌翻譯並不漫長卻充滿“論戰”的百年歷程,便於我國高等院校從事翻譯的師生、詩人譯者,尤其是廣大的譯詩愛好者,全面地瞭解我國詩學譯學理論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其發展趨勢;2017年又將進入到一個重新修訂的時間視窗,因為今年既是漢語新詩走完百年的輝煌之年,也該是新一代詩歌翻譯家共同彰顯百年詩歌翻譯實績之年。
中西詩歌翻譯史已逾百年,外國詩歌翻譯的實踐可追溯到晚清詩人蘇曼殊、馬君武的文言格律體翻譯,最早的白話譯詩在胡適嘗試白話詩的同時首開先河,五四運動前後,外國詩歌翻譯掀起了第一個浪潮。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魯迅、郭沫若、冰心、聞一多、徐志摩、朱湘、戴望舒、傅東華、施蟄存、鄭振鐸、朱生豪、梁實秋、馮至、梁宗岱、趙蘿蕤、孫大雨先生等在詩歌翻譯領域中做出了示範性的貢獻。魯迅先生早在二十世紀初就曾翻譯過德國詩人海涅的作品,後來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又介紹過普希金、萊蒙托夫、拜倫、裴多菲等詩人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很早就開始翻譯德國詩人歌德的《浮士德》,1925年翻譯出版了波斯作家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後來還翻譯過英國詩人雪萊、俄國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等詩人的作品。冰心翻譯出版過黎巴嫩作家紀伯倫的《先知》,巴金先生翻譯過俄國詩人普希金的《叛逆者之歌》;朱生豪先生更是中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先行者;傅東華先生翻譯過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史詩《奧德賽》以及英國詩人彌爾頓的《失樂園》;鄭振鐸先生將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詩歌介紹到了中國。那個時期從事詩歌翻譯實踐與詩論譯論構建者大多為詩人兼翻譯家,他們的新詩創作與翻譯實踐互為作用,共同推動著中國新詩運動的發展,迎來了中國新詩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文學翻譯事業蓬勃發展,新的詩歌翻譯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呈現,例如,1954年査良錚先生翻譯出版了普希金長詩《青銅騎士》,1955-1957又先後翻譯出版了《拜倫抒情詩選》、《普希金抒情詩》及長詩《歐根·奧涅金》。1955年方重先生翻譯出版了英國詩人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954-1962年間朱維基先生翻譯出版了但丁的《神曲》三部曲,1956年屠岸先生翻譯出版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方平先生翻譯出版了《白朗甯夫人抒情十四行詩集》,1957年錢春綺先生翻譯出版了德國詩人海涅的《詩歌集》、《新詩集》、《羅曼采羅》,1960年又出版了《德國詩選》。八十-九十年代期間,外國文學的翻譯蓬勃發展,詩歌譯壇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劫後餘生重建輝煌的老一輩詩歌翻譯家,如卞之琳、王佐良、羅念生、田德望、余振、戈寶權、袁可嘉、許淵沖、方平、飛白、楊德豫、江楓、屠岸、吳岩、錢春綺、湯永寬、王智量、呂同六、黃杲炘、馮春、張秋紅先生等為我國新時期文學的復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十世紀可謂是外國詩歌翻譯與中國新詩創作互為促進的時代,也是中西詩歌美學思想相互匯通的時代。一百年間古希臘、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義大利、西班牙、印度、伊朗等數十個國家的大量詩歌作品或早或遲地被介紹到了中國,史詩、哲理詩、抒情詩、敘事詩等五花八門的詩體成為中國詩壇的主角。經典外國詩歌作品不止一次、二次、甚至多次地被覆譯,個別經典作品,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有多達十個以上的譯本。步入新世紀以來,新一代詩人翻譯家出入譯界,為詩歌翻譯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他們遵循“詩人譯詩 譯詩為詩”的原則,在闡釋與重建詩歌文本的過程中吸取養分,融入到自身的創作中,為置身其中的當代漢語詩壇與譯壇帶來新的活力與繁榮。
縱觀我國百年的中西詩歌譯學理論,無論從“信達雅”、“化境說”到“多元互補論”,還是從“風韻說”、“形似論”、“神似論”到“三美論”、“三兼顧”等,中西詩歌翻譯實踐基本圍繞“直譯”或“意譯”、“格律”或“散體”、“音美、形美、意美”或“多元互補標準”等幾個方面展開,試圖解決“語言形式與內容關係”這一詩歌翻譯本體論主題。與其他各種翻譯相比,詩歌翻譯實踐有其特殊性,由於詩歌語言精煉繁複,比之其他形式的翻譯更能集中地體現對語言技巧的理解、把握與處理。中西詩歌翻譯的關鍵最終要落實到語言技巧處理問題上來,亦即形式與內容的協調問題;本體詩歌翻譯實踐討論的焦點也集中在特定的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上,客觀地看待我國至今在詩歌語言形式技巧與內容的協調關係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翻譯家各人間的分歧已然存在。
“一個人喜歡或建構什麼樣的翻譯理論決定於這個人具有什麼樣的氣質或個性。換句話說,翻譯行為和翻譯理論的走向常常受制於翻譯者或翻譯理論創建者的個性或人格”,北大學者辜正坤教曾在《譯學津原》(2005)一書中提出“玄翻譯學”這一重要問題,其理論意義絕不僅限於翻譯理論。當代許多詩歌翻譯家在翻譯理論和實踐方法上的分歧,都難越出這種個性的制約因素,例如,某個譯者譯得彆扭太直,則該譯者多半強調直譯的重要性;某個譯者譯得太自由,則該譯者多半強調意譯的重要性;某個譯者譯得講究韻律,則該譯者多半強調韻律的重要性;某個譯者譯得太淺白,則該譯者多半會強調流暢通俗的重要性;某個譯者的翻譯太注重形式,則該譯者多半強調形式的重要性;某個譯者的翻譯太注重神,則該譯者多半會強調創造性與意譯的重要性。當然這些論題都不是絕對單一的,主張直譯者並非主張絕對的直譯,在具體情況下也是可以默許變通的;主張意譯者也並非主張完全拋掉原作形式而任意胡來,而是認為原作形式一旦不便模仿,就可以大膽變通,在不違背原作本意的條件下發揮翻譯主體的創造性,各種譯論與實踐間可不同程度地兼收一種、二種或多種觀點的融合。
中西詩學譯學理論中涉及“語言形式與內容關係”的問題也是求真還是求美的大問題,西方古典主義詩歌追求形式技巧美,浪漫主義詩歌追求情美,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詩歌注重現當代的新奇多變,翻譯外國詩歌時最好根據不同的詩歌特點採取不同的翻譯原則或標準;也就是說,有時我們宜以譯詩的形式技巧美效果為目標,有時則宜以譯詩的情美效果為目標,有時則宜以譯詩的現代感效果為目標,由此確定相應的詩歌翻譯對策。因此,要厘定詩歌翻譯標準,首先要看標準針對的物件,只有事先搞清原語與目標語先天的語言學和文化背景的根本差別之後,才能確立詩歌翻譯標準的可能性所在。現當代詩歌在中西詩壇上的審美追求頗為相近相同,中西詩歌的對譯原則也比較一致,因為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詩歌是西方詩歌發展的產物,漢語新詩一直追蹤西方詩歌的軌跡,中西處理現當代詩歌翻譯標準應該比較一致。目前當務之急我國詩歌譯學理論與實踐更應發揮中西譯論優勢互補的原則,大力推動我國中西詩歌翻譯事業。近三十年間中西詩歌翻譯實踐發展迅猛,例如,詩人傅天虹創辦的《當代詩壇》僅十年來改版為中英雙語對照版大型詩學刊物,十分必要且意義深遠,而同時策劃出版“中外現代漢詩名家集萃”(中英對照)大型詩學工程必將為我國詩歌創作與翻譯實踐發展注入非凡的活力。
(海岸,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當代詩壇》副主編)

